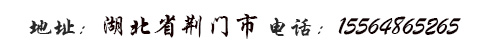卡达莱85岁的狐狸型作家,因写作抵达
|
济南治白癜风最好的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a_ht/140108/4323349.html 原创傅小平文学报 文学报 本周封面/伊斯梅尔卡达莱 (郭天容/绘) 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往往以独特的角度切入叙事,表达有着彩虹般异彩的多重主题,他那些篇幅不长的小说,也由此总是让人读出丰富、博大之感。自年成为首届国际布克奖得主以来,他就成了诺奖热门作家。 1月28日,卡达莱迎来了85岁生日。我们也似乎有必要在“卡达莱式的气氛”里谈谈阿尔巴尼亚出了怎样的卡达莱。 01 “他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 伊斯梅尔卡达莱往往以独特的角度切入叙事,表达有着彩虹般异彩的多重主题,他那些篇幅不长的小说,也由此总是让人读出丰富、博大之感。这颇为契合他孜孜不倦书写的阿尔巴尼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与中国情同手足,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眼里的“欧洲的一盏明灯”——所能给我们的印象。这个国度从地图上看像是一只耳朵,虽然疆域不大,人口不多,文学影响也在漫长的时间里甚少溢出本国,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体现在卡达莱的小说《H档案》里,两名来自爱尔兰的“民俗学家”为解荷马之谜,即前往阿尔巴尼亚南部偏远山区寻找仅存的古代英雄史诗。虽然小说写两人寻访史诗的举动被当作间谍活动,从而沦为一场“闹剧”,卡达莱却在某种意义上借这个故事进行了文化溯源。 以卡达莱另一部小说《三孔桥》的译者施雪莹的说法,阿尔巴尼亚从地理位置上看,是欧亚的交汇处;从历史进程上看,是新世界与旧世界的衔接点。这就决定了这个国家文化天然具有多元混杂的特点。而卡达莱出生、成长的那座靠近希腊边界的小山城吉罗卡斯特,就像他的好友、法国作家埃里克法伊说的那样,街道令人目眩的坡度、到处可见的石头、巨大而奇特的堡垒、凌空俯瞰一些街区的狱堡、德里诺河平原和环抱的群山的壮丽景观,凡此种种,都促使这位未来的作家逐渐形成敏锐的目光。卡达莱也在日后写的小说《石头城纪事》里感叹:“这座城市建造起来,仿佛旨在唤起伟大的思想。”在法伊看来,卡达莱戴着他的小城特制的有色眼镜观看全世界,将古代、中世纪和二十世纪融为一体,还把荷马、拜伦、十字军和意大利军车队混淆起来。童年的卡达莱更是收获了作家生涯的初步成果,他很早就阅读了《麦克白》,领会到名著可能具有的强大力量。 卡达莱故乡吉罗卡斯特远眺 多年后,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卡达莱回忆道,虽然当时阿尔巴尼亚的体制更有可能让他成为那种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年,他于首都地拉那大学历史与哲学系毕业,并获得教师任职资格后被送去高尔基学院,也是为了对他进行某种改造,他却对此已经有了免疫力。“早在11岁时,我就读了《麦克白》,它像闪电似的击中了我,我还读了希腊古典作品,有过这样的阅读之后,没有什么其他力量能够凌驾于我的精神之上。在我看来,埃尔西诺或特洛伊城墙附近发生的事,要比某一类悲惨平庸的现实主义小说更真实。” 这就能部分解释在中国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们在先锋文学思潮扫荡下,才有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的多元表达,阿尔巴尼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才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改革开放,卡达莱却早在年就写出了今天看来依然颇具先锋色彩,且被视为其代表作的小说《亡军的将领》。有意思的是,18岁即出版诗集的卡达莱写的诗,却有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同年,他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发表长诗《群山为何沉思》,当天便接到总书记恩维尔霍查的表扬电话,三年后,他发表了作为建党25周年的献礼之作——抒情长诗《山鹰在高高飞翔》,从此长期保持了国内桂冠诗人的荣耀。对于这种反差,卡达莱后来解释说,在那时的阿尔巴尼亚,诗歌更容易写,因为诗歌更适合用于歌颂。 《亡军的将领》封面,重庆出版社 事实上,国内文学杂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推介卡达莱时,也侧重于介绍他的政治抒情诗。但正因为写了这些诗歌,加之曾秉承上意写维护霍查孤立政策的小说,如《伟大的冬天》和《冬末音乐会》等,卡达莱始终受到一些争议。但这无损于他在小说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自年从马尔克斯、格拉斯、贝娄、马哈福兹、大江健三郎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届国际布克奖得主以来,他就成了诺奖热门作家,并接连斩获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耶路撒冷文学奖等国际大奖。如此,卡达莱的写作可谓应了国际布克奖评委会主席约翰凯里的话:“他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是一位世界性的作家。”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重庆出版社引进出版《破碎的四月》,开启了卡达莱再度“进军”国内图书市场的步伐。近年,随着花城出版社出版《石头城纪事》等近十部作品,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雨鼓》等三部作品,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事故》等作品,卡达莱的小说终于在我国有了比较完整的呈现。相比之下,《亡军的将领》最早于年作为“作家参考丛书”之一种由作家出版社引进出版时,印数只有区区册。如今,卡达莱终于在国内成了广有影响的大作家,以至于他的生日也成了忠实读者们庆祝的节日。不管怎样,读他的作品,我们有时也会如其小说主要中文译者、巴尔干文学研究专家郑恩波那样感叹,阿尔巴尼亚出了个卡达莱!今年1月28日,卡达莱迎来85岁生日。我们也似乎有必要在“卡达莱式的气氛”里谈谈阿尔巴尼亚出了怎样的卡达莱。 02 “文学是表达各种主题的手段” 倘是套用学者以赛亚柏林的概念,卡达莱大概会被归为“狐狸型作家”。他丰富的创作大体上都以阿尔巴尼亚为背景,如作家徐则臣所说,卡达莱要做的就是以他对这个神奇的国度的历史与现实的洞察,从中选取一些悖论性事件和命题,在某种困境里尝试展开自己的文学思辨。但卡达莱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他那些看似有着统一色调的小说,又会在细微之处体现出不同的原创性,以至于读他的几乎每部小说,我们都会忍不住感叹,他的创作何以如此独特。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卡达莱没有经历过战争。意大利法西斯年4月侵占阿尔巴尼亚时,他实足年龄只有三岁。但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他见过战争,他能感受到它,但这一点经历对于理解战争中的人性当然是不够的,卡达莱却在27岁那年就写出了深刻反映“战争”的小说《亡军的将领》。放眼世界文学史,这似乎也不是那么特别,托尔斯泰没经历过年俄国卫国战争,却以此为背景写出《战争与和平》。玛格丽特米切尔没经历过南北战争,却写出《飘》。但相比而言,卡达莱还是显得特别。因为他没有正面去写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却写出了比直接描写能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思考。小说写一个意大利将军在一个神甫的陪同下,到阿尔巴尼亚的土地上寻找阵亡者的遗骨,这似乎也不是什么引人入胜的题材,但如郑恩波所言,卡达莱把他所熟悉的甚至自幼就听到的种种故事,巧妙地编织在上面,采取故事中套故事,链环上结链环的巧技,多层面、多方位地展示各种人物对战争的思考和心态,就让这部小说变得丰富而又立体。 就像卡达莱自己感慨的那样,战争中的人性是复杂的。而他的这部小说写的就是战争背景下复杂的人性。他说,文学是表达各种主题的手段,我们能书写爱情或一些哲学的命题,我们也同样能书写战争,所以他选择了战争主题作为开始。但他当时太年轻了,并不指望创作出辉煌的、热情洋溢的作品,所以选择了一个悲伤的主题来呈现那个时代。而在文学中,悲伤总是比欢愉更能触动人心。 卡达莱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正是在于,他的小说总能引发我们与其中人物一样的情感。当我们说阿尔巴尼亚赋予了卡达莱得天独厚的写作资源时,我们似乎不能忘记如果他只是写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奇闻异事、风土人情,纵使写得再出色,也不过是优秀的民族作家。卡达莱在不少小说里都写到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习俗,但他显然不是展现习俗本身。举例而言,阿尔巴尼亚文化传统里有“拜萨”之说,意为“真诚”,特指一种“真心待客”的古老风俗,指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害做客之人,哪怕他是交战中的敌国之人,或是有世仇的敌对家族之人。他出版于年的《错宴》并非阐释“拜萨”之说,但如果没有这一习俗,小说里二战时德占期间古拉梅托大夫的邀请和他早年在德国留学期间的同学、德国指挥官弗里茨冯施瓦伯上校的赴宴,就缺少了正当的理由。晚宴后,弗里茨释放了被逮捕的阿尔巴尼亚人质,一触即发的杀戮危机得以解决。但正因为对当年晚宴中发生了什么提出质疑,阿尔巴尼亚解放后,当局就下令把古拉梅托大夫抓进了监狱,让他交代跟德国军官之间所谓的“猫腻”。预审法官沙乔梅兹尼为了一己利益,拼命折磨古拉梅托大夫,最后见目的无法达到,便丧心病狂地杀害了他。直到小说结尾,我们也不知道当年晚宴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读后也会觉得晚宴上发生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读出了人性的复杂和悖谬。 在《破碎的四月》里,卡达莱写到的在阿尔巴尼亚北部高原地区颇有传统的卡努法典,更是如翻译家余中先所说,几乎把“拜萨”的地位从传统改变成了“法律”。按卡努法典,如果一个人被杀死,他的家人必须为他报仇。小说里科瑞克切打死了乔戈的哥哥,乔戈就得为哥哥复仇,他于3月17日在路旁伏击仇人成功后,利用三十天的休战协定去城堡交血税,在路中与正在此地度蜜月的新娘迪安娜一见钟情,他想着在四月转成亡命的“黑色”之前的4月17日再次见到迪安娜,也恰恰在此时,仇家枪击了乔戈。卡达莱以诗一般的笔调讲述了一个人一个月的故事,却反映了一个民族几百年的困扰和悲剧性。人一降生就陷入一场追杀或者杀人的宿命中,生命便只能如破碎的四月般短暂和仓惶。 03 “宿命中隐藏着真相” 而卡达莱也仿佛是信奉宿命的那一类作家,他认为自己的宿命就是当作家——这是个非常困难的职业,存在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巨大竞争,每个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都在拼命试图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为此必须竭尽全力,这是一种痛苦的,也是幸福的折磨。而卡达莱的小说是或多或少包含了宿命感的。在他看来,虽然在阿尔巴尼亚文学里,“宿命”是被排除在外的一个概念,但这个概念从来就和文学紧密相连。他认为,“宿命”体现了人类思想的丰富性,也表现了人类思想的黑暗面,在“宿命”中也隐藏着真相,虽然这种真相非常难以寻觅。我们也分明能感觉到宿命感的萦绕,让卡达莱的小说多了一种艺术性和神秘感。 他的另一部代表作《谁带回了杜伦迪娜》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拜占庭和罗马教廷争夺公国的时代,弗拉纳也家的九个儿子在同一个季节相继死去,家里惟一的女儿此前刚被远嫁中欧。一夕之间,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家族只剩下一位老太太。可三年后的一个夜晚,远嫁的女儿突然被三哥康斯坦丁带回家中。老太太惊讶不已,因为康斯坦丁早在三年前就已葬入墓地;杜伦迪娜更是惊恐万分:在15天的路程中,坐在她前面的那个骑马人竟然是个幽灵!小说出版于年,正是阿尔巴尼亚选择彻底与世隔绝的时刻。于是,西方批评家从中读出了卡达莱以古老传说抵抗国家现状的含义:杜伦迪娜远嫁他乡,康斯坦丁“从墓中站起来”,开始漫长的穿越欧洲之旅,皆“来自和世纪交流的愿望”。无论这种读法是否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如该书译者邹琰所说,卡达莱却是借这一幽灵事件将阿尔巴尼亚的宗教冲突、战争灾难和分裂、闭关锁国的政治现实纳入自己的构图背景中,同时纤细入微地描绘了众生相。与此同时,小说里的阿尔巴尼亚没有具体的历史时期,但在这片阴雨寒冷的原野上,它却显得分外的真实。 更多时候,卡达莱把小说背景设置为遥远的人类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我们甚至可以说,卡达莱写的很多小说都是历史小说。于是,在《雨鼓》里,我们看到阿尔巴尼亚是一片多石的崎岖之地,15世纪的一天,奥斯曼土耳其大军浩浩荡荡开来,围攻这里的一座孤零零的要塞;在《耻辱龛》里,我们看到十九世纪初叶的奥斯曼帝国内忧外患,大小叛乱此起彼伏。京城中,奥斯曼皇宫的外墙上凿开了一方壁龛,即是叛臣和败将首级的容身之所——耻辱龛;在《金字塔》里,我们看到埃及法老胡夫遵从祖训,下令建造金字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越来越感觉到亡灵的召唤,分不清自己是死是活。而在《梦幻宫殿》里,卡达莱则将小说背景放在19世纪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阿尔巴尼亚,主人公马克-阿莱姆在睡眠与梦境管理局工作,这里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分类、分析成千上万个梦境,以便了解人民的所思所想,帮助国家或君主免于灾难。在有权的叔叔的帮助下,马克-阿莱姆青云直上。但有一次在破解一个意义重大的政治性梦境时,他却出了差错,结果给自己和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雨鼓》 《耻辱龛》《金字塔》封面书影 无疑,卡达莱的一些小说带有浓厚的讽喻色彩,作为一位精通修辞的诗人,他也如《纽约时报》评论的那样,有一种写起比喻来举重若轻的天赋,但纵使如书评人云也退所说,他写作技法高妙,能把荒诞的现实写得有如发生在另一个国度的寓言,削弱故事的刺激性,让一些保守分子难以抓到批判的口实,《梦幻宫殿》还是让他在国内“象征性”地遭到了放逐。年,霍查去世后,阿尔巴尼亚政局趋于紧张,卡达莱的一些作品无法在国内出版。自年开始,他陆续将几部小说以及一些诗歌的手稿分批带往法国。而按照当时阿尔巴尼亚的法律,绝对禁止“泄漏”文学稿件,他便将自己的作品伪饰成用阿尔巴尼亚语翻译的西方作品。他将手稿中的名字和地点替换成德国或奥地利的,假称其为西德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著作。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他每次只带几页,最终通过一位法国朋友两次飞往阿尔巴尼亚,将稿件全部带到了巴黎。而以他自己的说法,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让出版商在自己突遭自然或是“意外”死亡的时候,能将这些不为人知的作品迅速出版。那时他并没有想到几年后,年10月,因为阿尔巴尼亚政局激烈动荡,他不得不寻求法国政府的政治庇护,从而移居巴黎。 不过移居巴黎后,卡达莱并没有中断与阿尔巴尼亚的联系,毕竟如约翰凯里盛赞的那样,他是如此充满热情地描绘出了这个国家完整的文化——包括它的历史,它的热情,它的传说,它的政治和它的灾难。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家政治环境缓和,他每年都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回去居住。但卡达莱并不认为,一个国家政治环境缓和了,文学也会变得好起来。在他看来,作家不能让自己的创作因为政权的好坏而改变,而任何国家里的作家们应该都能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自由意志。正因为此,卡达莱才坦然道:“在知道自由时,我对文学已经很熟悉了,是文学将我引向自由,而不是自由带我走向文学。” 原标题:《卡达莱:85岁的“狐狸型作家”,因写作抵达自由 此刻夜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eboencheng.com/kbecrk/11070.html
- 上一篇文章: 北京二外本科生100可获跨专业学习机会
- 下一篇文章: 八十年代的阿尔巴尼亚欧洲的秘境一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