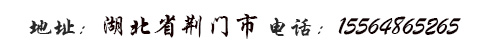怎么开出一个药方
|
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元宵节快乐!过年也是忙忙碌碌,很多天没有更新,话不多说,我们步入正题。 上一讲桂枝汤我们提到,开出一个方子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即便一个看似简单的桂枝汤,经过层层解析,里面蕴含的门道也是不少。 这篇文章,我们就从内容和立法等不同角度来认识一个方子。 一、从内容上分析 如上图所示。从内容上说,一个方子可以大概分为三部分:对证、对质和对病。这三个部分中,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单独够成一个方子。 1.1什么是“病”和“证” 首先,我们来区别下病和证这两个概念。 病,这里指的是中医中的病,包含了“病因、病象和病程”,可以理解为一个“人从正常状态到偏离正常状态最后到另一个状态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所有疾病的规律与特点”,这里的“另一个状态”或许恢复原本正常的状态,或许是另一个稳定的正常状态,或许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病态,或许仍然是不稳定的病态到了另一个新的病程。对病,即“辩病论治”,针对的是病理病机,强调始发病因和病理过程,是通过局部治疗以改善整体。 证,包含了“病象、体征以及能为诊断提供帮助的表征现象”,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一般由一组相对固定的、有内在联系的、能揭示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病变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构成。对证,即“辨证论治”,强调机体的整体反应特性,是通过整体治疗以改善局部。 如上图所示,病和证都需要从人的体征和症状来描述,所不同的是,对病治疗是通过症状和体征来判断疾病,以疾病的为中心来治病;对证是通过症状和体征来判断身体状态,以人体的身体机能为中心来调整身体状态。从空间上讲,证包含了一个人此刻的所有体征和所患疾病的性质,所以证更多是面向空间的。从时间上讲,一个病在其病程中会呈现各种证,所以病更多是面向时间的。 当然,我们辨别“病”和“证”不是为了完全将二者割裂,而是将二者统一起来,进行诊断。辩病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认识病机。辩证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的状态。辨病论治是治病以治人,辨证论治是治人以治病。在开方前,分析病机和辩证论治是同样重要的。比如太阳病是辩病,太阳中风是辩证。确定了是太阳中风证,我们就能开出桂枝汤调和营卫,祛风解肌。确定了太阳病,我们知道太阳病,病在表,当以汗法治之;还能知道如果失治或者误治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变证;还可以根据病程的时间特性来判断此病什么时候可以痊愈(太阳预解时)。 1.2各部分特点 对病部分的专病专方或针对性药物,比如针对偏头风的散偏汤或者半解汤;比如针对扁桃体发炎的北豆根、牛蒡子。这种方子的特点如下: 1.指向性强,时方中多见。金元之后,尤其到了明清,医家用药也更多地立足于局部的症状,采用针对性较强的药方或药物。 2.药的选择范围广,用量和配伍灵活。 3.结合现代药理学研究成果,以此为理论指导中药的使用。比如常用的抗癌药物,白花蛇草、半枝莲和蒲公英等。 对证部分的方证或从方证中提炼出来的药对组合,比如针对少阳证的小柴胡汤;比如从小柴胡汤中提炼出来的和解少阳的药对“柴胡-黄芩”。这种方子特点: 1.整体感强,经方中多见。方子立足于人的整个机体,从整体出发,通过调整机体来达到治疗的效果。 2.用药精炼,药的选择范围固定,用量和配伍严谨。 3.与古中医学、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和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对质部分虽然作为独立的一个部分,但是在方剂中是一般是融入在前两部分之中的,也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我们所开出的药方首先要考虑到个体的差异,也就是患者的体质。当我们对辩证环节胸有成竹的时候,心中已经有了合适的方剂,这时候还要再根据患者体质调整下个别药物的用量。 当然这部分也可以单独存在,比如很多人在没有不舒服的时候,也可以根据个人体质的情况用中药进行调理。比如柴胡体质的可以用小柴胡汤、逍遥丸、四逆散和温胆汤等方剂加减调理。 1.3三者关系 现在来看下对质、对证和对病这三者的关系。在下层的部分是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方框越高代表这部分所占的比重越大,或者说是诊断开方的核心环节。 先看体质,辩质。我们面对一个人,不是一上来直接切他的脉,而是先应该观察下这个人的体态,也就是“望诊”;然后跟听他说话的声音,注意他说话时候口中的味道以及身体上的味道,这就是“闻诊”;之后,可以问问他以往的病史,平时的身体素质,饮食起居习惯和工作性质等,这一步是“问诊”;有了这三部,就可以基本确定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偏热还是偏寒(寒热),偏实还是偏虚(虚实)。有了这些背景信息,我们再问问有什么不舒服,看下舌苔的情况,最后进行号脉。这些基础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中医看病跟西医不同。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打败疾病,而是让人恢复健康,治病只是恢复健康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水到渠成的效果。看到一个人说话声音低,表情黯然,脸色无光,即使是麻黄汤证,我们在切脉的时候也应该看看他胃气和肾气是不是充足。这就是先辩质会给我们后面的论治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看一个身体偏瘦易饿,声音高亢,易激动的人(阴虚阳亢体质)患了外感风寒,问下他之前每次着凉是不是都嗓子不舒服,我们在给他辛温发汗的同时,就应该考虑下这个辛温的药会不会助内热,再或者应该考虑到还没等他喝药,外邪就已经入里化热,上攻咽喉。这就是辩质会给我们预测未来病势走向提供依据。 现在我们来讨论“对病”和“对证”这两部分。“对证”的高度最大,说明了我们开方时候,辨证论治,对证下药是最为关键的。一个中医看一位病人,肯定是看他有什么症状,各种生命体征的表现,然后结合舌脉诊来确定方子。 看病人有“汗出、恶风、头项强痛、脉浮缓”,不管你是外感类型的太阳病,还是营卫不和的内伤杂病,我都用桂枝汤进行加减。这就是异病同治,为什么能同治,因为同证。 都是浅表性胃炎,症状胃痛呕吐,一个脉沉紧舌淡苔白,一个脉弦数舌红苔黄腻,那么前者就是属寒,脾胃虚寒证,需要用吴茱萸汤、理中汤和良附丸等加减来温中;后者属热,脾胃湿热证,需要用左金丸、温胆汤和三仁汤等加减来清热燥湿。这就是同病异治,为什么需要异治,因为证不同。 由此可见,最终决定我们用药方向的是证,寒证热证、表证里证、虚证实证用药肯定不同。 一张方子有了“对证”这部分,即使没有“对病”部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比如,一个失眠的患者,我们判断为“心火亢盛,心肾不交证”,用了交泰丸,那么不加酸枣仁,柏子仁或者磁石这种安神类药物,也能药到病除。 那么对病这部分又有什么作用呢?上文提到了,病更具时间特性,从你身体偏离正常状态就可以算是病程的开始。那么当我们在“辩证”时看不到明显的症状,舌脉也看不出明显异样(或者医者水平问题分辨不出来),或者根据现有症状辩证后,用药无效,那么不妨换个角度,从“辩病”的角度切入来分析病机。 郝万山老师讲伤寒论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么一则医案。郝老师当时跟诊宋耀志抄方,遇到一位病人过敏性哮喘,经服用过中西药可以缓解急性的症状,但始终无法根治。宋老师问了这位病人当初发病的原因,原来当初这个人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五一节有时候北京的天气是很热的,他走得又热又累又渴,直接喝路边的自来水是管子的凉水,喝了很多,又吃了好多自己带着的油饼。结果,游行没有结束他就开始喘了。宋老师又看了下舌脉,开出了一个很简单的栀子豉汤的方子。果然服用了三周之后病人就不再来了,后来郝老师又遇到这位病人,他说后来每年也没有复发。 再比如,之前提到的散偏汤。病人偏头疼经常发作,发作时候痛苦不堪,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偏头疼,只要是疼肯定是伴有气血瘀滞和清阳不升,而且发作时候应该急则治其标,等用后症状缓解了,我们再去辨证论治,深究这里面是因为气血不足还是痰湿壅滞或是阴虚阳亢等。 可见,分析病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角度进行切入,为辨证论治提供一个有力的补充。 二、从“理”“法”的角度分析 面对一个病人,两位医生开出了不同的方剂,病人吃了都有效果。两位医生在分析病程时出于不同的“理”,采用了不同的“法”,开出了不同的“方”。 “理”就是“医理”,不同的“理“就是围绕不同的立极点展开医理阐述,这些“立极点”就是医者所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eboencheng.com/kbecrk/8964.html
- 上一篇文章: 你的皮肤还好吗
- 下一篇文章: 这十种最适合室内种植的水养植物,你养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