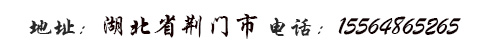雷德侯中国艺术史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领
|
白癜风治疗的医院 http://www.pfb1.net/m/ 雷德侯教授访谈录 中国艺术史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领域 (德)雷德侯 (LotharLedderose) (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 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艺术的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 吴若明 (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 吴若明:您好,雷教授。早在20世纪60年代,您就已经开始学习汉学,相信当时这个专业学习的德国人并不多,您是如何对其产生兴趣,并走进东亚艺术研究领域的呢?您的父母对您在东亚艺术文化上的浓厚兴趣培养方面有何影响? 雷德侯:汉学在二十世纪中期对于欧洲人来说,确实是属于“冷门”专业,了解的也不够多,但是对我而言,学习汉学却不是一个偶然。我的父亲当时是科隆音乐学院(HochschulefürMusikK?ln)的钢琴教授,我的中学时代是在科隆度过的。那时候我虽然还在读中学,但常去科隆东亚博物馆,要知道,在德国至今只有两个专门的东亚博物馆,一个在柏林,即我后来工作过的柏林东亚博物馆,另一个就在科隆,而且科隆东亚博物馆还是德国最早建立的一所亚洲艺术博物专馆。我非常感谢那时候的科隆东亚博物馆馆长史拜斯先生WernerSpeiser(-),也非常佩服他。当时的科隆东亚博物馆是二战空袭中的牺牲品,被完全破坏了,而新馆还没有建好,庆幸的是馆藏的近千件文物基本没有受损。即使在战后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史拜斯先生还是成功的主办过多次展览,一些特展常常是在科隆当时的城市大门那里举办的,吸引很多人参观。 我的父母本身并不是收藏家,但是他们都非常喜欢东亚艺术,他们觉得这是很有独特魅力的艺术品,所以我也常有机会一起去。久而久之,我和史拜斯先生就熟悉起来,我喜欢跟随在他身边学习这些来自遥远的东方古代的艺术品,了解它们,接触这一领域,这也是我高中时期最大的兴趣所在。特别是常跟随史拜斯先生就在被战争破坏的原科隆东亚博物馆建筑旧址内,坐在那些破损的墙壁上,去亲手触摸这些古老的东方文物,听先生娓娓道来它们的名字、生动有趣的功能和在另一种宗教文化下的社会意义,这些都深深触动着我的心。更让我感觉遗憾的是,在德国欧洲的艺术史一直以来有那么多人去研究,而和其相媲美的亚洲艺术,研究者却少之又少,实在可惜。正是在这些影响下,我在高中时期就产生了将来要从事东亚艺术这一领域研究的愿望。 吴若明:在您的研究历程中,您最初选择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的书法,特别是如篆书和行草,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都很难阅读。很多欧洲和美国的东亚艺术专家也似乎更倾向于绘画和器物上的研究,而您最早出版的两本书恰好就是一本是写清代的篆书,第二本就是米芾,这位以行草著称的书法家。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雷德侯:中国的艺术本是一个广大的范畴,它涉及的面非常广,青铜器、书法、绘画、瓷器、玉器、金银器、佛造像等等。然而,我个人认为,书法是中国艺术和文化的中心和基础,也是中国最为广泛的一种艺术形式。很多中国的艺术品,其创造者和收藏者都有一定的范围限制,或文人阶层,又或流行于贵族。而书法是最没有界限的,中国古代的大部分人都会写,都在用,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中国古代所有立志于仕途的人都首先练习和精于书法。它是从实用的书写中产生,又逐渐成为艺术品,因此我最初就选择了书法。篆书是中国古老的书法字体,它的美是中国古代一千五百年以来具有连贯性的美。你可以看到我的客厅中仍摆放着碑刻拓下的秦代的篆书作为屏风,而这些秦代篆书的艺术,直到清代仍在审美和风格中具有连贯性,我个人非常欣赏清朝的篆书家们,他们在风格上反复临摹了先前的这些规范化的书法作品,又创作性的发展并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这样的特定艺术形态而具有独立风格的复合性风格结构,是中国书法作品特有的,在世界艺术中也是特别的。 相对于较古老的篆书、隶书而言,草书、行书和楷书是在六朝时期后出现的,而这之中草书是最早的,它是从篆书,特别是隶书中衍生出来,最初为了书写便捷,但很快固有的美学特性使其成为一种新的字体,它的艺术自由性让它总出现在非正式官方文书等场合。行书也源于隶书,但形态更接近楷书,和草书相比,省略部分略少,但同样具有自由发挥的特性。这种飘逸的字体非常适合文人。我在完成对清代篆书的研究后,开始对米芾的行书以及草书等书法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不仅仅是研究他的作品本身,也注重研究他的书法理论。 [德]雷德侯著 我很钦佩米芾,因为他不仅仅是个书法创作家,也是一个杰出的书法理论家,当然他在山水绘画上也颇有成就。米芾的美学思想是书法力求超逸、平淡、天真,他注重艺术鉴赏,强调书法的学术性和知识性,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个人风格。同时米芾在临摹和研究中国书法作品的传统源泉,又或最高标准,即晋代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主的著名书法家方面非常有造诣,他对经典作品的解释也很精辟。而这些在继承中国传统古典艺术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也是后来书法鉴赏的标准,在我看来,非常重要。 吴若明:在您学习汉学和东亚艺术的过程中,您的学习背景非常丰富,包括了德国的科隆、波恩、海德堡,以及巴黎、普林斯顿及哈佛大学,还有台北和东京。您知识背景的形成和知识体系的构建对于更深入的研究东亚艺术有何助益? 雷德侯:现在欧洲、美国等地已经在大学中将汉学系和东亚艺术史完全的分开了,前者更注重文化、文学社会等方面,后者则专注于古代艺术品。并且还细分有日本学专业。而在六七十年代,没有这么细致的区分。汉学也包括了中国的考古、艺术史等各方面。直到现在,尽管德国的大学大多设有汉学专业,而专门的东亚艺术史专业,则主要在柏林自由大学和海德堡大学。 多元化的学习背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让我获益颇丰,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专于汉学,又同时在东亚艺术,包括中国和日本等艺术方面的广泛学习。我在德国最开始学习的是欧洲艺术史和德国文学,这些对于我在后来在东亚艺术史研究中经常会和欧洲艺术相比较,也更容易发现中国艺术的独特性,同时中国的艺术不是孤立的,和欧洲艺术史有共通性,而一些基础的艺术史理论和方法论也对于之后东亚艺术史的研究都适用的。 我在德国博士毕业后去了美国,接触更多的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了解前沿动态。正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和岛田修二郎两位教授促成了我研究米芾的动机。当时的中国内地并没有像今天这么国际化,方便去学习,我于是去了台北,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看到很多的书画作品,对米芾的研究、翻译等工作也得到更好的进展。我的中文名字雷德侯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先生赠送的。 日本的艺术和中国艺术具有很多共通性,同时很多日本的学者如铃木敬先生在中国艺术方面的研究在世界上都很有影响。我在日本的研究工作,让我更好的掌握了研究中国艺术的方法,比如我在《万物》中写到的《地狱十王图》章节,正是之前在铃木敬先生的研究小组内跟随其所做的调查基础上完成的。同时东京的西川宁教授和京都的中田勇次教授都是中国书法研究的专家,对于我在中国书法的研究也很有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万物》中对于中国古建筑部分的研究,特别是古代木塔,在历史中的完好保存是非常困难的,日本奈良南部的法起寺(始建于年),这个和中国的建筑方式一致,而又完好保存的古老木塔则给我很好的研究实践机会。他们允许我在塔内细节处充分拍照,完善了我在中国建筑的研究工作。此外,我在日本期间也积极学习日本传统艺术,因为在东亚艺术史研究范畴中,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包括韩国的古代艺术,这是一个整体且具有共通性。 [德]雷德侯著 对于日本艺术的学习,是在研究中国艺术中多了一个积极有益的比较面。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仅仅是中国艺术史的老师,同时也负责日本艺术的教学工作,这些工作后来由更偏向日本艺术研究的特埃德教授(Prof.Dr.MelanieTrede)承担。目前在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学习东亚艺术史中国方向的学生,我们仍鼓励他们同时学习日本艺术,并要求他们至少完成一个日本方向的课程及作业。在基础理论的学习中,也是作为一体的。 吴若明:您的研究领域涵盖了中国艺术史各个方面,不仅仅有书画、青铜、瓷器,还有中国的传统建筑,并且在建筑史学上也颇有见解。您是如何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eboencheng.com/kbecyy/5398.html
- 上一篇文章: 10月24号富士康26元H,伯恩26元,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