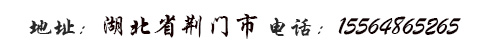技术与制度融合视域下中小学校的组织功能
|
上世纪80年代,以迈耶(JohnW.Meyer)和斯科特(W.RichardScott)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对教育组织领域的制度与技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在他们看来,正式组织结构的产生肇始于两种过程。“一是在复杂交换的技术与社会环境下,开发理性化的科层组织结构旨在有效协调技术工作;二是社会出现的制度结构将特定类型的角色和方案界定为理性与合法的双重属性,这些结构鼓励发展涵盖这些要素并遵守规则的科层组织”[]。现代学校作为一种正式化的教育组织,应以协调发展教与学的技术为重心,还是以反映并遵从社会赋予学校的制度与价值期待为首要任务,已然成为基础教育领域必须明确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一直受制于制度环境与学校技术的复杂互动。 在论及学校组织结构问题时,我们习惯性地将技术与制度分开甚至对立起来。新制度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组织:技术型组织和制度型组织。“技术密集型组织倾向于对技术进行严密监管与控制,通过调节技术流动使其免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技术与制度环境隔离,组织成为相对封闭的系统。与此相对,制度化的组织将其结构与更大的制度环境建立的框架紧密联结。制度化的组织倾向于从内部实际技术工作活动中缓冲组织结构,通过使用认证、授权、保密和仪式等技术,试图将其技术工作从组织结构中分离出去,以便与制度环境紧密联结”[2]。一、背离制度环境的学校技术 组织研究大多强调技术支配逻辑和工具性特征。受此影响,正式组织被视为是协调和控制活动过程的有机系统。基于效率至上原则所设计的正式组织会努力确保组织结构与技术活动之间的紧密衔接,而将技术从制度环境中缓冲隔离,以更加严格地管理和控制技术。学校常被隐喻为一个履行“输入—转化—产出”功能的生产系统,技术(教与学)作为将输入原材料(学生)转化成为合格或高质量产品的关键,构成衡量一所学校办学质量的主要标准。因此,对于学校而言,缺乏达成预设教育效果的技术手段和高质量的输出生源,意味着组织的合法性与资源支持将深受威胁。奥利弗(OlibverChristine)认为“技术功能上的压力会导致去制度化过程(Deinstitutionalization)”——如果制度化实践在技术绩效方面存在问题,必然要求与制度环境脱钩”[3]。这也是当下教育市场呈现出资源愈发多样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原因:家长和学生将优先选择设定较高学业目标、拥有优秀的教师和管理者以及较强的绩效责任系统的学校。换言之,受教育者及其家长将首选教学技术强大、输出生源质量高,而非是严守制度的学校。那些在课堂教学、课程开发等方面具有独特之处或显著优势的学校,倾向于形成技术型的组织架构,最大程度减少来自制度环境对学校核心技术的干扰。需要指出的是,结构与过程的合法性同实质性的生产效率并非保持绝对意义上的一致性[4]。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并不总能获得合法性,披着“合法性”外衣的技术手段往往也会遗存效率低下的痼疾。例如,以“高考工厂”闻名的衡水中学因其高升学率而获得众多家长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eboencheng.com/kbechb/9766.html
- 上一篇文章: 万科拟分拆ldquo万物云rdqu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