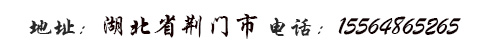这,就是约翰加尔文第二部属于两个
|
第二部 属于两个城市的人21—24章 茜亚凡赫尔斯玛著王兆丰译/张艳芬校 第二十一章 约翰加尔文这个29岁的的法国难民牧师,不仅以安提阿换了所多瑪,他自己似乎也改变了。他不像以前那样容易激怒,他更能听别人说,也更愿意学。他在日内瓦的那段时间里,显然没能顺利地传福音。他仍然在思考日内瓦所发生的事。在给法雷尔的信上加尔文写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不够老练......我们被神管教是应当的。“ 在斯特拉堡,加尔文愿意“按此地的规据,掰饼喝杯。虽然他不允许接生婆为新生儿施洗,因为这与神的话直接相违背,但对于教会里一些不太重要的事,他也能容忍,并且也劝法雷尔说:“我们要尽力劝弟兄们不要为那些小事争论......” 他所教的学生们再也没有人带着剑进来。但对于他们穿着不整洁,不端庄他不会提高嗓门。他还告诉法雷尔:“也不必把纪律定得那么严,以免搞得人人胆小慎微“。加尔文身边火焰般的法雷尔换成了布舍。他成为一位繁忙的牧师,教师和作家。他很享受在这个法国难民的小教会牧会。他的讲道吸引了许多周围地区说法语的人。他也小心地依照布舍所使用的教会敬拜顺序,那是从路德宗来的。他们满怀激情地歌唱令人兴奋不已。年加尔文出版了一本诗歌集,其中有18首“诗篇”和“使徒信经”。有些曲子是他谱的,另一些是克莱芒弗拉特作的曲,他就是年加尔文在意大利的弗拉拉城堡遇到的那位诗人。 加尔文将原来想在日内瓦教会实行的事一件一件付诸实践。年春,他的会众投票采纳了斯特拉堡其他教会所用的教会纪律。他们也很喜欢自己的牧师。他常出各家控访,他爱他们,教导他们,给他们讲道,领他们掰饼喝杯。 加尔文也被任命为斯特拉堡高级中学的圣经老师。此校后来成为全欧州最杰出的学校之一,校长是来自巴黎著名的约翰斯特姆,也是加尔文的好朋友。除此以外,他也答应给城里的公民教圣经,就如在日内瓦时那样。他写信告诉法雷尔“我每天不是教课就是讲道。” 他在这里完成了“纲要”的拉丁文第二版,比第一版大得多。他也把这一版翻译成法文,翻得极美,以至后来人们称加尔文为现代法语之父,正如路德因将圣经翻译成德文而被誉为现代德语之父。 年10月他的“罗马书”讲稿付诸印刷。这是加尔文写的许多极为纯正,精辟的圣经注释中的第一本。他也写了一本关于教会敬拜顺序的小册子,解释了他认为什么是根据古教会的,最好的敬拜顺序,其中也包括圣餐的方式和简单的婚礼仪式。 接着他出版了“简论主的圣餐”一书。共有6个短章节,是以法文而不是学者所用的拉丁文写成的。加尔文希望普通百姓也能读,因为当时在教义上最大的争论就是圣餐。在此教义上,路德,慈运理,教皇,加尔文和他们的跟随者们都不能达成共识。奇怪的是,这位法国难民的牧师竟成了裁缝协会的会员。那时,一个人若不加入某一行业的协会,无论是屠夫,木匠,还是铺路工,卖布商协会,就不能成为斯特拉堡的公民。 为了成为公民,他从羞涩的钱包中挤出了20福林交给裁缝协会。他是否真有裁缝天份,还是他教课的地方离裁缝协会很近而加入,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约翰加尔文自从离开祖国法国之后,第一次成为一名公民。 然而,在此安宁城市中的这个大忙人,还是有他的麻烦和伤心。他一贫如洗,就如在日内瓦一样,斯特拉堡议会答应付工资给他,但又把此事情忘了。等到他们发现时已经六个月过去了。他的工资是每星期1福林,勉勉强强够他的生活费。他在给法雷尔的信上说:“眼下我几乎撑不下去了,但只要是我欠的账,一旦有能力支付,我一定全数还上。眼下我口袋里几乎一文不明“。 他和法雷尔仍欠他们在巴塞尔的房东钱。房东寄来一张帐单,其中包括一瓶葡萄酒的钱。可加尔文记得这瓶酒是别人送的。他写给法雷尔,算出了各自应付的部分:“我们不必客气......你住了七个星期又二天,我住了两个月又十二天......我就这样算:我付5个金先令,你付4个。但我欠你一个半金先令,只要一有机会我一定付还给你......我大概一共有20个巴塞尔先令。“他一分多余的钱也没有了。 有人主动愿意来帮助这个穷牧师,杜蒂耶从法国写封信来“您目前的处境大概不妙。假如您生活实在困难,请您不要在意......假如您愿意,神允许,我会支援您“。 杜蒂耶在此信中建议加尔文可以回法国,并暗示可以回到罗马天主教。加尔文回信说,他确信神带领他在斯特拉堡,在抗罗宗教会服事。他不想花朋友的钱欠任何人情债。他很有礼貌地回信:“您主动提出要帮助我,实在令我不知如何来感谢您......但我不敢再给您增添负担了......在过去的年月里您已经为我花费了太多了“。 不久,一个说话很敬虔的骗子来找加尔文。他听上去是那么好的一位基督徒,说服了这个穷牧师借给他十八金法朗,加尔文不得不自己再去借一部分凑足款子,他留下一只蓝子,说里面是他的财产作抵押,以表诚意,很快就会归还。 加尔文在一封信里写道:“几个月后他回来了,微笑着-不,是嘲笑着-问我,是否愿意再借些钱给他,我告诉他我需要那笔借给他的钱“,骗子什么也没说就消失了。一年半之后,加尔文决定打开他留下的那只篮子,他请来了斯特姆校长和另外几位朋友,一起打开,看见了里面的宝贝:几个烂李子,几件破衣服,几本旧书和一些从别人那里偷来的信件。尽管是受害者,他也与众人开怀大笑起来。 在布舍家住了一阵子后,他去租了一栋房子,一些学生也搬进来合租,但麻烦也不少。有时学生付不出房租,有时那个说话粗鲁的女管家会引起一场大乱,有时候加尔文自己也会被头痛,胃痛折磨失去控制而发脾气。加尔文告诉法雷尔说,有一次他完全失去控制,原因是那个一度在洛桑任牧师曾指责日内瓦的牧师们不信三位一体的卡罗利再一次宣布从罗马天主教转到抗罗宗,也再一次离开法国跑到瑞士,跑到斯特拉堡来。加尔文和法雷尔决定忘掉从前的事,以爱心接纳他,假如卡罗利真的改变了的话。但他却是再一次来进行搅乱。他在斯特拉堡试图说服布舍和其他传道人,起来怀疑加尔文。几位传道人和卡罗利一起草了一份关于信仰教义的声明,签了名,当晚送到加尔文那里要他签名。这几位传道人为了要达到和睦相处,同意了卡罗利的思想,但其中许多加尔文是不同意的。 假如他签名,就对不起他的信仰,若拒签,卡罗利就会指责他远离朋友,一个人独来独往。加尔文非常气愤,要求牧师们一起开个会,他们决定在其中一人家里的晚餐上讨论。加尔文写信告诉法雷尔说:“那次我犯了大罪,不能控制自已的情绪,竟被怒气冲昏了头脑,向众人发火”。 他接着写道:“这里当然有令人引起义愤的原因,但我若能在表达时有节制就好了......我表示自己宁死也不会同意......我跑了出去,布舍跟了出来,用他合情合理的话使我安静下来,劝我回到屋里......回到家后,我痛悔不已,痛哭流泪,几乎不能控制。“这是一位基督耶稣的仆人,一个与他自己的罪挣扎的人,他在失去控制之后,痛苦地流泪。 在斯特拉堡还有更多的事令人悲痛,令人流泪。那是在加尔文来此一个月后,当时他还住在布舍家,传来了盲人牧师库劳德去世的消息。传说他是在奥口沃比地区的一个镇上传道时遭人下毒而死的。加尔文在给法雷尔的信上说:“库劳德的死令人痛苦得几乎崩溃,甚至白天的忙碌也不能令我忘怀......白天的忧虑和苦恼只是在准备晚上更痛苦,更痛心的思考,我不仅仅是因由此而引起的失眠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整夜忧郁沮丧缠绕着我......这种残暴的行为不是没有原因的......主让我们这些人尚在世上存留,让我们在已去了的弟兄所走过的道上坚忍下去,直到跑完我们的路......“ 不仅库劳德离世去了,在意大利弗拉拉公爵夫人宫里的奥里维坦也死了,年仅32岁,据说也是遭人下毒而死。先是另一位传道人遭害,下一位是他的表弟,就是加尔文在巴黎时从他那里听到改革宗信仰,加尔文也为他翻译的法文新约的圣经作过序的那位表弟。他们不仅在信仰上,也在血缘上紧紧相联。 幸好加尔文在斯特拉堡并不是孤单一人。学校,教会有他许多的朋友,还有同父异母的妹妹玛莉亚,弟弟安东尼。若干年前,他俩离开家乡挪扬与这位出了名的哥哥在一起,他们在巴塞尔住过一段时间,可能在日内瓦风风雨雨的那二十个月也在那里,现在他们能与他一起住在斯特拉堡,使他很高兴。然而布舍的话不时在他耳边响起:“你必须结婚。” 第二十二章 加尔文写信给法雷尔说:“我们希望新娘会在复活节之后就来此地,你若确定会来,我们的婚礼就一定等到你来......我要求你来......你也曾保证过你会来......我最希望的就是你来。“这场原计划要请法雷尔来证婚,祝福的婚礼并未发生。此后也没有再提及那位预料在复活节之后会来的女士。在朋友们催促之下,五月在给法雷尔的信上又提到了结婚的事。他告诉法雷尔他对心目中人的要求:“我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对方的美貌就会不顾一切堕入情网,连对方的败坏行为都照样接纳无误的人。吸引我的美乃是:朴实无华而富有耐心,不过分挑剔但善于勤俭持家,最好也愿意照顾我的健康“。 到了来年2月,这位牧师还在盼望他的婚事,在给法雷尔的信中说:“在此种种混乱之中,我对自己竞厚颜的想要娶妻这件事,倒还觉得平安。有人也曾为一位出身贵族的名门闺秀提过亲,据说还有大量的陪嫁,两件事使我不愿与对方交往。一件是她不懂我们的语言法文,另一件是我担心她会太看重她的名门出身和贵族教育。她哥哥是位敬虔之人,极力想促成这门婚事......她嫂嫂也很热衷......后来我回答说,除非对方愿意学习法文我才能订婚。对方要求给她一点时间考虑。但后来那位贵族小姐不愿意学法文。“这件事提醒加尔文不应再往前走,他接着写道:”这以后,我请弟弟和一位德高众望的人一起去代我向一位女士求婚。认识她的人都极力推荐说她人品极好。“这位侯选取人会带来的大堆陪嫁不是金钱而是德行,他继续写道说:“假如事情顺利-我们当然是这样希望-那么婚礼会在3月10日前举行,我希望你能光临,为我们祝福。不过,这一年多来我已过份地麻烦你了,这次我不敢要求你来......不然的话,这次结婚的希望若再次落空,我就实在是个傻瓜了。“ 这次的希望还是落空了,加尔文不打算进入这个婚姻。3月29日给法雷尔的信上说:“我们的婚事又暂告停顿,我自己也极受困扰。”那位女士催促着要成婚“,除非主让我失去控制,我不会娶她,但拒绝她又是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尤其是牵涉到那些好心人,我真巴不得能够从此窘境中脱离出来。” 加尔文成了问题的焦点。他怎样才能有礼貌地拒绝一位不想要的人呢?只好找弟弟安东尼,他是此事的红娘。这件事使加尔文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他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极其小心,免得再陷入这种尴尬局面。到了6月,他在信上说:“我还是没有找到妻子,常常为此事忧虑不决,不知道我是否还需要继续努力。” 接下来是年8月,加尔文结婚了。法雷尔从纳沙托来为他们证婚。加尔文在自己的会众中找到了新娘。一旦找到她,他们没有久等就成婚了。新娘是位有两个孩子的寡妇,除了符合加尔文所列出的所有条件之外,她还非常美丽。 依多莱特戴波尔来自吉德兰省,现属荷兰。前夫是做生意的,叫斯多迪阿,是在斯特拉堡听了加尔文讲道之后从重洗派改信改革宗的,不久死于那场瘟疫。 加尔文再也不可能找到像他现在这样的妻子了。但是从结婚开始,法国牧师这位善良的妇人一直没有全部拥有过她的丈夫。搬进加尔文住的那栋学生公寓,首先遇到的是那位尖舌的女管家。但依多莱特从来抱怨过。她不仅富有耐心,甘心服待丈夫,乐于分担主交结他的工作,她自己也常去探访病人,安慰受苦之人,与人分享她的信仰。 妻子的爱使加尔文得到了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幸福。布舍说得对,结婚很好,特别是娶一位善良的太太。难怪法雷尔也向他推荐说要结婚,尽管他自己已过五十还是个单身汉。 他俩婚姻上的乌云是身体软弱与疾病。在给法雷尔的信上加你文说:“就好像是命定的......神对我们过分的喜乐作了调整,叫我们不致因我们的婚姻而忘乎所以。“婚后不到一个月,夫妇俩就开始被疾病所缠。 在此同时,又与女管家发生矛盾。那是一个礼拜一早上,女管家对弟弟安东尼说了很粗鲁的话(她常常这样),安东尼一声不响地离开那栋房子,并发誓说只要女管家在,他永远不来。接着是女管家自己也出走了,因为她看到加尔文对安东尼的事那么伤心。但她儿子仍在那里,那天晚上加尔文吃得过多,“我经常如此......当生气或被极大的忧虑搅扰时,就会滥吃......以致第二天早上都被不消化所折磨。“平时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什么也不吃,但这次他担心管家的儿子:“我若拒绝,他会以为是间接地表示要辞掉他”因此尽管胃不舒服,为了不伤这个年轻人的心,他还是吃了。 下午讲道时就感到很难受,晚上竟晕了过去。接下去就是发冷又发烧,每隔一天发作一次“我病得几乎连手指都抬不起来。”他还未恢复之前,妻子又因其它原因发烧,“连续八天来她病得都坐不起来。” 在九年的婚姻中,两个病人一直被疾病所缠绕,但却没有抱怨。幸福已经叫他们知足-他们因对方而知足,因神决定送到他们生活中来的一切而知足。 第二十三章 神的工作是不能等到完全恢复健康的,甚至身体还在发着烧,加尔文与卡皮多,布舍他们“一起工作,就好像我很强壮似的。” 重任就在眼前,神圣罗马帝国的意大利查尔斯皇帝想要使罗马教廷与抗罗宗合起来,他需要此联合,为的是要来对抗正从东边压境的凶悍的土耳其大军。在此紧迫的情形下,若能把抗罗宗的日耳曼各国与罗马联合起来,对他极为有利。 于是皇帝决定安排几次会议,这些会议被称为帝国议会。从年到年共举行了4次。日耳曼各省和那些自由城市都派出代表与会,每个省的王子都以当地教会的官方代表出席,每次会议都少不了漫长的辨论和谈判,双方代表每天都发生冲突。 加尔文作为斯拉堡的公民,被这个日耳曼的自由城市作为代表派去参加。他只是一般的代表,无论如何,他不过是个法国人,被这个德国城市派作代表已经是件荣誉的事了。此外,他对此类会议并不包括希望,怎么可能使罗马教廷与抗罗宗手拉手到一起呢?他在给朋友信上说:“对我自己来说,我并不抱希望。”但他那双鹰眼却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仔细地分析每位带领者,每次主要的辨论,他在给法雷尔的长信里有详尽的述说,就像当时的一位驻现场记者一样。会议上也讨认各种国际事务。 会议上,加尔文在这里遇见了日耳曼各省的王子们,神学家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马丁路德的右手人物菲立浦墨兰顿。加尔文于年春在法兰克福遇见他,俩人之间的友谊迅速发展起来,一直持续了24年,直到后者去世。墨兰顿比加尔文大12岁,极有学问,在多种语言上,学术上卓有建树。21岁那年被任命为威登堡大学的希腊文教授。他为人随和,友善,但有时太过于友善而在一些本该坚定站立的事上倾向于妥协。他的性格特点与他的主人路德正好形成鲜明对照。 墨兰顿第一次遇见加尔文时一定对自己说:“原来这就是那个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熟韵古教会先父们的年轻人哪,在那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后面是一颗什么样的脑子啊!“在一次会议上,墨兰顿给他的法国朋友起了个外号。那次加尔文将一位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驳得体无完肤。从此以后,墨兰顿与人谈到加尔文时,都称他为“那位真正的神学家。”要知道,从墨兰顿嘴里出来的这个名字,实在不是恭维而是赞赏。 加尔文称墨兰顿“具有无以伦比的知识......敬虔与美德,值得任何世代的人钦佩。”后来加尔文在给他的信中说:“我不过是个后生晚辈”同时他也亲密地以名字而不是用姓来尊称对方。然而,当这个德国人太急于妥协,调和,太不愿意对德国众教会注重诸多的仪式而缺乏纪律的事上站出来,加尔文会毫不迟疑,直截了当的地当面向他指出。他在写给法雷尔的信上说:“对于这些事,我当着菲立浦的面直接向他提出。” 一方面,加尔文相信自己在圣经所教导的教义上站立得岩石般坚定,另一方面,他也能从未停止过努力催促,使抗罗宗教会的合一。只要这些不牵涉到基本教义,他愿意忽略教会中那些人为造成的不同。在给法雷尔的信上,提到布舍时加尔文写道:“他不同意在这些存争议的仪式上我们应与路德分离,我当然也不认为这些是促成不和的理由“。 在神话语所教导的教义上,加尔文毫不妥协。但他仍花大量时间,努力使其他人也相信他所相信的。在给法雷尔的信上说:“我事先已经写信给菲立浦,说明了我对达成协议的事所作的声明。我与他作了许多讨论。“这位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讨论的一个重大主题,是关于主的圣餐。基督的身体是怎样体现在圣餐里的?饼并非像罗马教廷的追随者们所说的,转变成为身体。在这点上,他俩很快就同意了,但是基督的身体是否象路德所坚持的,是与饼同在?在饼的上,下还是在其中呢?加尔文以圣经为据,说基督的身体和血不是在物质上与饼和葡萄酒同在,基督的身体和血是属灵意义上存在于圣餐中。“在与墨兰顿讨论之后,加尔文高兴地写信告诉法雷尔:”对于墨兰顿自己来说,你不必怀疑,他与我们看法完全相同。“这是不是路然宗与加尔文之间取得一致意见的开头呢?问题是,在赢得温和的墨兰顿之后,也能赢得墨氏的主人和那些德国王子们吗? 抗罗宗的另一边是瑞士改教家慈运理的一派。他们跟随慈运理,在关于圣餐中主的身体一事上,认为圣餐是一种纪念基督之死的仪式,他们不如加尔文注重此事的属灵圣礼。因此,加尔文是站在路德宗与慈运理派之间,他想要一边伸出一只手将这两派联合在一起。他在写那本“简论主的圣餐“一书时就是抱着此希望的。他想要使这本书成为有利于抗罗宗各派讨论的基础。他在书中的语言是坚定的,同时也是很小心的,他没有用他常用的一些强烈语调。 年马丁路德在一家德国书店里读到这本由法文译成拉丁文的书后说:“早知如此,从一开始我就会将这件有争议之事整个地交给加尔文,若反对我的人也如此做的话,我们早就该和好了。“ 马丁路德从未见过约翰加尔文。这位伟大的德国改教家在写给朋友布舍的信上说:“请代我向斯特姆和加尔文致敬,我特别喜欢读他写的那些书!“墨兰顿告诉加尔文说,路德常常提到关于他的事。加尔文在给法雷尔的信中说:”菲力浦......在信上说,路德和波米拉诺斯特别要求问候加尔文,他们很看重加尔文。菲力浦还告诉我说,有些人为了刺激路德,把一段我写的批评路德和他的朋友们的文章拿给他看,路德仔细地读了那段文章后说,我希望加尔文有一天会把我们想像得更好些,无论如何,他今天就应该知道我们对他的好感。“加尔文接着说:”假如我们不被这种温和的反应所动,则真是石头一般了。对我自己来说,我为此深深地被感动。“ 几年后,当路德开始在圣餐之事上大动感情地发火时,加尔文站出来为他辨护。他写信给慈运理派的领神:“我们必须记往路德是何等伟大的人“他列举了路德的伟大事绩之后又说:”即使他称我为魔鬼,我仍然尊敬他,称他为神的好仆人。“ 加尔文也写了封信给路德,那是路德临死前几年。当时他变得非常易怒,时常发脾气。墨兰顿没有将此信交给路德。他向加尔文解释说:“我设有把你的信转交给马丁博士。现在他容易多疑,对于你在信上提出的问题,他不想让他的回答被人传来传去。”在加尔文的这封未送到收信人手里的信里,他附上了一些他写的东西,请路德评论,并加上一句说:“假如我能飞到您那里,哪怕是短短的几个钟头与您在一起,我也会很享受......但知道在此世上我们没有得到此机会,我希望很快我们就会在神的园里相见。再见,最著名的人,基督最出色的传道人,我永远尊敬的父亲。“ 若是神选择使改革宗的巨人们在他话语的基本真理上合起来,谁能想像得出抗罗宗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假如那一天曾临近过,那就是诸如加尔文,路德和墨兰顿这样的人能够面对面,或通过信件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的那天。尽管有分歧,他们仍将对方看作是基督里的弟兄。今天我们或许能从这些伟大的改革家们身上学到一课。 第二十四章 加尔文哭了。他几乎被抽泣所窒息。他将脸埋在双手之中。 在这位哭泣的人面前,是一封信。几位骑马来的信使跑了几百公里路,将这封信送到他手里。他们先是到了斯特拉堡寻找那位法国牧师,议会告诉他们,加尔文牧师在沃姆斯,他代表我们城市在那里参加第三次帝国议会。 信使骑马继续向前奔去,进了沃姆斯的城门,穿过热闹的街市,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收信人。他们庄重地将信交人他。 “福音的执事,加尔文博士敬启”这是写在信封上的字,里面则以更亲切的口气写道: “我们满怀热情地向您推荐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确信,除了要推动,展示神的荣耀,神的神圣话语之外,您别无他求。我们谨代表小议会,大议会和全体日内瓦人民......我们迫切地请求您能回到我们这里来,回到您的老地方,老事工上来,我们盼望,在神的帮助下,此事将会大有益处,将会结出更多的果子。我们的人民极盼望您回到我们中间。他们愿意,并且一定会以您满意的方式待您的。将会结出更多的福音果子。“ 您的好朋友 日内瓦行政长官暨议会 年10月22日 蜡封的议会公章上刻着日内瓦的警句: 黑暗之后是光明 现在,这位被如此想要请回日内瓦的人坐在信前哭了。信使们表达了他们自己的请求之后走了。坐在加尔文周围的是斯特拉堡的会议代表们。他请他们来,要听他们的意见。交谈中,他两次不得不离开屋子,不让那中断他讲话的眼泪流出来。 “请你们帮助我”,加尔文乞求他的同伴们:“告诉我该怎样做”,请勿考虑我和我的感情,唯一考虑的是何种方式对福音的增长,对神的荣耀最有好处。我一直被痛苦缠绕。你们知道,我已为这决定挣扎了许久,但我没有答案。我所信靠的朋友们,请帮助我,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斯特拉堡的人们诚挚的回答说:“我们的好弟兄,你知道我们城市是多么想要留住你。其实,当日内瓦的信使们到斯堡之后,议会特意派了快马来告诉我们,不要对日内瓦作任何许诺,要我们留住你。若是依我们看什么是对基督最有利的,我们就巴不得将你留在斯堡,但神若另有旨意,我们怎能挡住你的路?不过请留下来,等到这次会议结束,再考虑你当如何行“。 20年前,马丁路德在沃姆斯勇敢地站立在皇帝面前说:“我站在这里。我心无二愿,上帝啊,求你帮助我!”这是路德的永垂不朽的话[注:当年路德在此勇敢地为自己的抗罗行为辨护]。现在加尔文也在这座城里,远离自己的家,远离新婚的妻子。他与其他代表们挤在旅馆的一间大宿舍里。9月的那场疾病使他身体仍然很虚弱。等待期间,他与墨兰顿在一起私下讨论,辨论有关信仰上的各项事情。墨兰顿就是在此给他起的外号叫“那位真正的神学家”。几百名与会代表们越来越焦急不安,因为会议还不知道何时能开始,大会主席格兰维尔公爵还未来到。一个月之后他终于来了。接着几个星期,讨论大会的日程和辨论方式,最后终于在年1月14日,辨论正式开始。加尔文在此足足等了两个半月。 二个半月里,他一直在为日内瓦的事挣扎。这不是新问题,这封送到沃姆斯的信并非出于意料之外,只不过是在他的重担上加上了份量。日内瓦的这付重担从未离开过他,哪怕是在离开这座叛逆的城市,成为和平的斯特拉堡公民之后。离开日内瓦五个月之后,加尔文曾写信给那里的教会;九个月后又写信去安慰,劝告弟兄们要以爱和睦相处,年9月,他花了6天的时间,写了封1万5千字的长信给那位想要把日内瓦劝回到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那是一封怎样的回信啊,主教大人从此闭上了他那张善于雄辨的口! 这位颇有学识的红衣主教叫撒道来特。年4月,他写了封恭维,劝说的信给日内瓦。在信中,他以华美词藻盛赞了日内瓦和她的人民。他说“那些到处惹事生非的抗罗宗们,在贵城忠心的罗马天主教里闹起如此的风波,实在令人伤心。如今,你们日内瓦人民胜利地将这些闹事的牧师们赶了出去,我们是否可以以真实的爱心邀请你们回到母教的怀抱,回到那永世的罗马教会“? 日内瓦无人能给撒道莱特的这封感人的信作答覆。后来,加尔文的朋友们将信送来,请他帮着回信。他能拒绝吗?不仅要帮助日内瓦不致回到罗马去,他自己也仍然是日内瓦的一份子。他给红衣主教回了封信。加尔文以日内瓦教会的名义告诉撒道莱特:“当神将我放在此地,令我永远对此教会忠心。关心此教会的安全是讨神喜悦之事。因此,当我看到日内瓦教会所面临这最险恶的网罗时,我当尽上最大的努力......谁可以来劝说我对此事保持沉默,漠不关心呢?“ 加尔文给撒道来特的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加尔文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争执。此争执影响,决定了他的一生。首先,此争执的关键并不在于宗教改革的观点,即:称义的教义,神职人员的滥权,人为的圣餐变体,向圣徒祷告,教皇的特权等等,这些后来都会论到。对于加尔文来说,在所有这一切底下,最根本的问题是神的荣耀之中心性,绝对性。这也是加尔文一生从头到尾的目标。 他在信里对主教说:“你那种对天堂生命的热心,是使一个人完全献身于他自己的热心。即使是以圣洁神的名义,也是为要激励他自己”换言之,哪怕是关于永生的宝贵真理也可以被歪曲,偏离到用来代替神而成为万事的中心与目标。这就是加尔文向罗马教廷的最大挑战。这在他日后的写作中一再,一再地出现。接着他向撒道莱特指出他应当如何行,这也是加尔文一生致力的目标,即:教导人,让人知道人生最主要的动力应该是热心展示神的荣耀。[注:此段引自“欢乐的主权遗产“,作者是约翰派尔帕。 在斯特拉堡,加尔文不断地听到关于日内瓦的消息。教会的四位新牧师是软弱的人,情愿跟随众人,其中两人是伯恩派来的。城里的放荡生活变得更放荡,有人甚至吹吹打打地在街上裸行。 终于,对此的抵抗也渐渐开始。议会通过了更严格的法律,虽然他们没有执行。那四个反对加尔文的行政长官下了台。其中之一因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另一同谋则从城墙上跳下摔死了。另外两位行政长官迅速逃之夭夭。他们曾策划将日内瓦交在伯恩手下,那两位伯恩派来的牧师也走了。 在这一切不安之中,人们越来越觉得没有加尔文那只坚定的手日内瓦无法生存下去。早在年3月,赶走加尔文还不到一年,朋友们就写信希望他能回来。加尔文耸耸肩,在给法雷尔的信上说:“我宁可死一百次也不愿背那个十字架。在那里我一天要死一千次,我将此事告诉你......请你务必尽全力阻止任何想要把我拉回日内瓦的努力。“ 洛桑的那位可爱的维勒特牧师也听到了传说。他写信鼓励加尔文,考虑回日内瓦,并说那里的新鲜空气和良好气侯对加尔文的健康会有好处。加尔文苦笑着回信:“我读到您信上的那段忍不住要笑起来。您表示了对我身体健康的关心而推荐日内瓦......我宁可干脆一次死掉也不愿到那个地方去受煎熬。因此,我亲爱的维勒特,若您真的希望我好,请不要再提此事。“ 秋,议会采取了行动。9月21日小议会委托议会领袖培林,设法将加尔文请回来。10月13日议会决定给加尔文写邀请信。10月19日,大议会决定“为了上帝的荣耀得以彰显,务必要请加尔文来做牧师“。次日,日内瓦人民集合起来,人们喊着:”我们一定要加尔文回来“,并一致决定派专人去斯特拉堡郑重邀请约翰加尔文回来。 此后,信件,特使不断地来找加尔文。日内瓦又请抗罗宗的伯恩,苏黎世去说服斯堡。苏黎世答应去试试,可是伯恩却毫无兴趣,因为他们想控制日内瓦的目的一直未能达到。许多人私下写信给加尔文:“快来吧,弟兄啊,得胜地来吧,好叫我们因我们的救主神而喜乐!”另一封信上说:“请不要说『不』,那样您就是在拒绝圣灵而不是拒绝人。日内瓦教会很重要......没有人能像您那样有智慧,有能力,有力量地来带领我们的教会。那两位留下来的牧师从前曾反对加尔文,现在也说:“我们在基督里尊敬的父啊,您属于我们,主自己将您给了我们,人人都盼望您来。” 维勒特答应到日内瓦作6个月的代理牧师,并写信说:“不要再迟疑了,快来建立这个正陷于痛苦,悲哀和后悔中的教会吧。” 当然还有法雷尔。只要有人去斯堡,他就会送去一封“炸弹”。第一次就是他命令加尔文留在日内瓦的。加尔文在挣扎中给法雷尔回信:“你那轰在我头上的炸雷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竟让我心里充满了极大的恐惧和惊愕。你知道此事会令我生畏,我并不是聋子,你为什么如此激烈地攻击我,几乎要危及我们之间的友谊呢?“ 年10月23日,加尔文极有礼貌地从斯堡写信给“尊敬的,荣誉的日内瓦议会与行政长。大人,我可以在神面前向您们证明,您们的教会对我来说是何等重要。在她需要的时候我决不会袖手旁观......另一方面,我也不能不经过正常手续,途经就突然离开神召我在斯堡的服侍......此外,斯堡议会已决定要我与其他代表一起出席沃姆斯会议,我不能单单为一个教会服务......我向您们保证,我不会拒绝任何我能做的事,只要神允许,我会尽我的全力来服待您们。“ 收到特使们送来的信后,他从沃姆斯给日内瓦又写了封信:“我可能还需要出席一个帝国会议,一旦我得以从此项工作中脱身,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们,假如斯堡教会和议会同意放我的话。“在给法雷尔的信上:”当我想到我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时,我将我的心作为祭,献给主......我将我的灵魂捆起来顺服神。“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即使这意味着回到日内瓦去,回到他在给维勒特信中提到的”这是天底下最可怕的地方“去。但是,加尔文人性的一面挣扎着不愿回到那座湖上城市,在那里他会“一天死一千次,”他写信给催促他回日内瓦去的苏黎世牧师说:“若是按我自己的感觉去做,我宁可到大海的另一岸也不回那个地方去。“ 随着日子渐渐过去,要作的决定已经明显起来。在给维勒特的信上,他说:“不知怎么的,我也说不出是如何发生的,我开始倾向于做回日内瓦的决定了。“做这个决定虽不愉快,但却是明确的。斯堡教会也答应,尽管布舍坚持说这只是暂时的,等到日内瓦教会稍有好转走上轨道后,他就该回到斯堡来。 斯堡议会说,我们仍然保持你的公民身份,也继续支付你的工资。加尔文将公民身份作为议会对他的尊重接受了,但工资他拒经了。 沃姆斯议会失败了。皇帝宣布休会,第四次会议决定设在法国的拉提斯堡。年1月23日加尔文和同事们回到家里。他们离开斯堡整整三个月了。在家住了一个月后,又上了路。拉提斯堡的路途遥远,多恼河上的冰部分解冻,斯堡的代表们可以从水上走。他们乘大筏子将行李物品用毛皮包起来以免结冻,马匹,书籍,炊具也都浮在筏子上。告诉法雷尔“我很不情愿地被拖到拉提斯堡去,我可以预料这次行程不会顺利......我很怕到时候会议又拖得很长久,这种会可以拖十个月之......但我必须跟随主的带领,他最清楚为什么要让我走这条路。“ 在拉提斯堡期间,他们听到瘟疫正在斯堡肆虐的可怕消息。每个人都为逃命离开那里。依多莱特去了她哥哥那里,弟弟和妹妹逃到了邻近的一个小镇。那个法国难民弗雷是位老师,也是加尔文最亲密的朋友,死了。那位全房客的儿子也死了,他父亲最以他为骄傲,加尔文从斯堡写了封极感人的信安慰那位父亲。 他写信给法雷尔“我日夜都在思念妻子。她孤身一人,无人安慰也得不到支持。”这个斯堡来的人焦虑,痛苦地等候着会议的召开。 三月,四月,五月,辨论进展缓慢,好容易有了点协议,但圣餐的事像以前一样,又成了一堵墙。加尔文不断地写信给法雷尔详细报道:“菲力浦和什舍对圣餐变体起草了一个大胆然而不真诚的理论,试图想要满足对手但又毫不相让。这两位好人怀着最良好的心愿,也未存其它的目的......只想要推进基督的国度。“这种努力不会有结果的,他请布舍放他回斯堡去,布舍不太情愿地同意了。 加尔文长途跋涉,于6月25日回到斯堡。除了见到依多莱特的高兴之外,这次回家是很凄惨的。在他自己的家里,在许许多多的家里,到处是被瘟疫带走的人留下来的空位子。加尔文四处探访,安慰众人。他依依不舍地看着斯特拉堡他所熟悉的人们和地方,就好像是对他们说,再见了。 日内瓦和其它瑞士城市的信不断到来。他已经在神面前许了心愿,他还得再等吗?“你要等石头喊叫起来吗?”法雷尔在最近的信里吼了起来:“假如当年你离开日内瓦时你也像今天这样拖拖拉拉的话,事情可能就不致于像现在这么糟糕了!“。 日内瓦议会派了特使来接加尔文,要护送他去日内瓦。斯堡议会虽不情愿,但还是让他们的牧师走了。他们给日内瓦议会写了封信:“他终于到你们那里去了,这是一个无可比拟的,主的少有的器皿。我们的这个世纪里没有出过像他这样的人,真的,除他之外,你们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年9月初,加尔文随日内瓦特使离开斯堡。他和妻子商量好,由他先去,然后再通知她晚些去。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睛,加尔文骑上马离开了这座他度过了三年的和平城市。这是富有成果的三年,神将他送回日内瓦的暴风雨中去。没有人知道,连加尔文自己做梦也不知道,几年之后他的法国难民教会竟被皇帝下令离开这座和平的德国城市。布舍也被迫流亡英国。没有人知道,他要去的那个狂暴的城市会变成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改革之城。 年9月13日星期二,两位骑在马背上的人走近日内瓦的科那文城门。耸立在前面的,是圣皮埃尔的钟楼。 全付武装的百夫长从头盔下看到了两个人,第一位骑马的穿着日内瓦特使的礼服,手持国旗。后面那穿黑衣的是谁?他再看一眼就知道了。 这就是日内瓦全城都在等候的那一位。 欢迎 分享 转发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eboencheng.com/kbecrk/925.html
- 上一篇文章: 名企有约9月20日招聘会职位查看,名
- 下一篇文章: 2016欧洲杯24支球队23人名单出炉